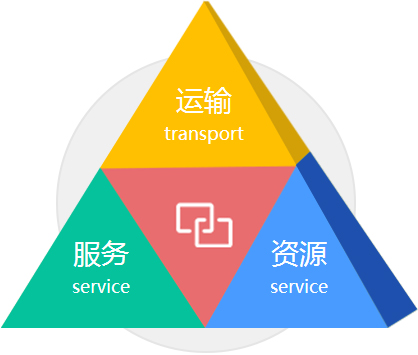實際上,就蒙古包的歷史溯源,則遠不止1000年。我們追溯其源頭,能發現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祖先們早期建筑文化的歷史遺跡和今日蒙古包居住形式的最早端倪。
由考古學得知,在人類生活的早期,居住的問題就存在了,但居住文化的形成,特別是人工住所的營造,卻比人類早期生存的歷史要晚許多。從今天遺留下來的中國古代文獻資料和地下發掘出來的文物看,生活在華夏大陸上的中國人的始祖,大約是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才開始有意識地建造房屋的,也就是說從那個時代起,文明的曙光才逐步展現出人類居住文化的迷人景觀。而生活在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即今天蒙古民族的祖先,他們居住文化的形成當也在這個時間前后。
洞穴是古代初民的居所,從中國其它典籍文獻的記載看,無論是古代中國南方先民的巢居,還是北方先民的穴處,都是中國人的祖先在最遠古的時代的居住方式,他們是利用天然的山洞、樹洞作為休息和生存的場所的。
在中國各民族多種多樣的居住類型中,既有從事農耕的民族固定的住房形式,也有從事狩獵、游牧的民族移動型的臨時住房形式。簡易的帳篷是古代中國北方游牧民族長期使用的一種居住形式,中國古代典籍文獻中稱之為“穹間”。可見,流動和搬遷是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特點。
在許多中國古代典籍文獻中,把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稱為“毯帳之民”,把中國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所使用的蒙古包的雛形居所稱之稱“穹廬”、“氈帳”、“旃帳”等等,是有一定道理的。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才出現“氈房”、“帳篷”、“蒙古包”等說法。
通過上述文獻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作為真正意義上的蒙古包的形成,還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的。
遠古時代的人類的始祖因地制宜,改造利用現成的自然條件,或住天然洞穴,或居樹上。到新石器晚期,才學會自己制造“洞室”,在地面挖一個地洞,沿洞壁用木頭、石頭之類壘起來,與洞沿壘齊后,再在洞中栽一排木桿,與木石之墻取齊,用一些簡單的長木桿綁制成梯子,供人出入之用。同時兼有走煙、出氣、采光、通風等多種功能。等到這樣地穴式的建筑搭建在地面上后,上面提到的木桿和通風口就發展為后來蒙古包的編壁、門和天窗。
屬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語民族、通古斯滿語民族、蒙古語民族都把這種洞室式建筑稱為“烏爾斡”。“烏爾”這一詞根的本意就是“挖”的意思,至今仍應用于衛拉特蒙古語的口語中。但在普通蒙語中,“烏爾斡”一詞已經專指蒙古包天窗上的頂氈而言了,引伸為“家”、“戶”、“居民”等意,這可以看作是歷史陳跡在語言學上的遺留。
隨著原始人類由采集向狩獵過渡,他們的活動范圍越來越大,同時也把一部分食草動物逐漸馴養成家畜,出現了畜牧業文化最初的胚胎。這種經濟文化模式要求一種便于遷徙的居室,于是窩棚之類的建筑應運而生。這種窩栩式的居所再向前邁進一步,原始的支架就變成了現代意義上的蒙古包的“哈那”(即以木條為材料用皮繩縫編成菱形網眼的網片),與上面提到的由洞頂演變的天窗結合在一起,便有了蒙古包的最早的雛形。
這種居住方式完全是由北方游牧民族的經濟文化模式所決定的,他們沒有固定的住房,住的是用木竿和氈子搭起來的帳棚,圓形,不用時可以隨時折疊起來,卷成一團,當作包裹。當他們必須遷徙時,把它們一起帶走。
到了公元七世紀前后,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游牧人的住所多為皮棚。那時生活在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多以狩獵為主要謀生手段。他們把獵獲的野獸皮剝下來,覆蓋在木頭支起的架子上作為住房,我們在近現代鄂侖春獵民居住的“撮羅子”上依然能看到這種皮棚的影子。在現代蒙古語中,“失勒貼速”(漢語意為“編壁”)為“哈那”一詞所取代;“格爾”這個詞泛指一切房屋;“干魯格”一詞則專指蒙古包天窗的氈簾。有趣的是,蒙古語稱“地穴”為“干魯格”,由此人們可以大膽推論,蒙古包是由古代游獵民的皮棚或地窩堡發展而來的。
到公元八世紀前后,中國北方的游牧民族逐漸脫離皮棚,住進了氈包。《蒙古秘史》所說的“干魯格臺兒”或“失勒帖速臺格兒”,意思是“有天窗的房子”和“有編壁的房子”,就是指蒙古包而言,也就是漢文典籍文獻中所說的“穹廬”、“氈帳”,有的典籍文獻也稱之為“帳幕”。實際所指都是一個東西,即現代蒙古包的雛形形式。